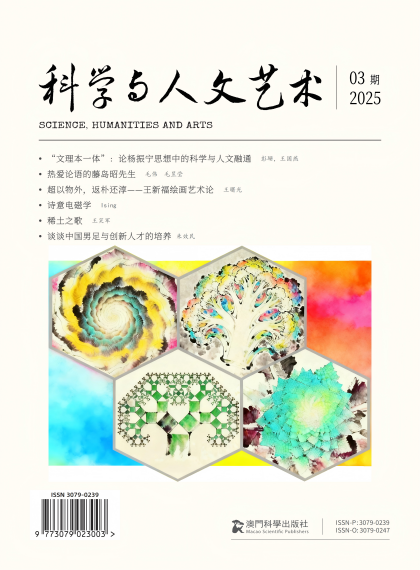一、导论
1959年,英国科学家和小说家C. P. Snow在剑桥大学的演讲《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中指出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对立给现代社会带来实践知识和创造性层面的巨大损失,具体体现在实践、知识和创造性方面[1]。以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突破,在提升社会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催生人文精神的危机,削弱人本身的整体性、伦理性和审美性[2]。科学与人文的关系始终是思想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议题[3]。
该背景下杨振宁的思想正好提供了一种独特的中国视角。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除了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卓越成就,杨振宁在科学与人文的融通思想方面也展现出中国式哲学智慧。他长期关注于科学与文化、人文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在他的科学研究、教育理念以及文化论述中,“科学之美”“科学的文化属性”“科学与艺术的相通”等是被经常提到的词汇概念,在其看来科学不仅仅是一种理性的探索,更是一项审美与精神的创造活动[4]。
梳理人类科学思想史,可以发现杨振宁“科学与人文融通”理念的思想源头可追溯至更早的探索。爱因斯坦倡导“宇宙宗教观”,他虽不信奉人格化的上帝,却敬畏自然和宇宙规律,认为真正的宗教情怀与科学精神相通,是人类追求秩序与和谐的重要动力[5],这与杨强调“科学的美与真理的统一”相契合。“社会生物学之父”爱德华·威尔逊在《知识大融通》中提出从科学出发整合人文的“融通计划”,主张突破学科界限,实现知识的整体化,而杨的融通思想具有更强的东方哲学色彩,注重科学与人文的双向关联。首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物理学家汤川秀树认为“物理学与诗的世界相通”,以东方哲学的“共感”思想理解量子场的连通性,与杨一样试图以东方精神贯通现代科学,但汤川更倾向形上的诗意直觉,杨则以数学与对称性为路径。
这一思想可概括为“文理本一体”的整体观[6]。本文以此作为理论框架,对杨振宁思想中科学与人文的内在关联进行系统梳理,追溯其思想的理论渊源,并结合三个层面的思想实践来引出现实启示,进而揭示这一科学与人文融通观念对于当代科技社会的文化价值与教育意义。
二、杨振宁的思想渊源与理论结构
深入分析杨振宁的思想渊源与理论结构,其本质是在中西文化交汇中逐步形成一种复合性思想体系——根植于西方科学理性传统,并汲取中国哲学里有关整体性的深层智慧。个人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家庭背景与教育经历等因素。早期,杨振宁的文化底色深受其父杨武之的启蒙影响。杨武之是著名数学家和教育家,曾留学于芝加哥大学,兼具中国传统学养与西方学术训练。其父在思想上主张“学问不必皆为实用”“无用之学方为至学”,杨振宁的求知取向因此受到了一定影响。童年时期的杨振宁成长于清华园中,父亲会在教授数学逻辑知识的同时引导他阅读和学习中国古典诗词、历史著作等。杨振宁自幼便打下坚实的数理基础,逐渐形成对文化审美的敏感。这种“文理并育式”教育为其后来的科学美学意识埋下了根基。
青年时期,在西南联大接受人文与科学并重的教育是杨振宁思想成型的关键阶段。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以“通才教育”与自由学术精神闻名,在教育理念上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如此学术训练下,杨振宁跨学科知识和能力得到增长。不仅如此,他还接受了梅贻琦、叶企孙、吴大猷等一批科学与哲学兼通学者的指导。长期浸润于这一崇尚思想独立与精神自由的学术氛围中,杨振宁形成了对“整体知识观”的初步认知:科学的意义不仅止于求真,更应参与人类精神世界的建构。
此外,赴美求学与恩师恩里科·费米的学术风格也对杨振宁的科学哲学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费米以“化繁为简”的理论风格著称,追求理论的简洁、优雅与逻辑自洽,反对过度形式化的复杂推演。杨振宁也继承了这一特点,反映在其自身上为:“科学研究的核心重在揭示自然规律背后的对称性、简洁性与优雅性,这些本身即具有审美意义”[7]。这种对称性与美感的追求使杨振宁逐渐意识到,科学的根本使命并非单纯解释世界,而是揭示人类心灵与宇宙秩序之间的和谐。也正是在这一思维维度上,他开始将科学视为一种文化与精神活动。
杨振宁的思想并未止步于西方科学理性的传统范式,而是逐步超越,转而从中国传统哲学中寻求一种更具整体性的世界观。他指出中国文化的核心在于整体观与和谐论并非分析与分割,始终以天人合一为最高境界,关注人与自然的统一关系[8]。这一观念与儒家“中庸”、道家“天人合一”、宋明理学的“理一分殊”等思想一脉相承。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杨振宁在《中国文化与科学》一书中提出,中国文化若能与现代科学精神结合,便能孕育出新的人文科学文化形态[9]。
与这种中西融合的文化理想相呼应,杨振宁晚年将目光聚焦于“科学之美”的哲学阐释。在2001年清华大学《美与物理学》的演讲中,他讲述了“美”在科学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像狄拉克这样以极简、纯粹、逻辑严密著称的科学家,其精神特质可与高适诗句中“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相媲美,甚至如同袁宏道笔下“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型诗人。而相比狄拉克的明晰简洁,海森伯则以感性直觉为起点,在不确定中逐步逼近真理,其探索性正显示了原创的活力。杨振宁认为,这两种风格都印证了理性与灵感、逻辑与直觉、美与真之间存在深层的统一。正是在对科学审美经验的深刻体悟基础上,他将这一思考上升为哲学层面,逐渐形成了关于科学理性、美学精神与文化价值相互融通的整体观念。
通过对中西思想的吸纳与整合,杨振宁最终形成了一个多层次的“文理本一体”理论结构,体现为理性、审美与文化的统一。他以科学探究的逻辑为出发点,认为自然具有深层的数学结构之美,强调科学理论必须具备逻辑自洽和可验证性,其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论正是这一立场的体现,科学进步依赖于理性分析与实验检验的结合[10]。在科学实践中他重视美感的作用,认为最高层次的理性与审美具有一致性,科学创造常源于对美的感知,美感也成为评判理论的重要隐性标准[11]。最后,他将关注点落到科学的文化意义上。科学的终极意义并非在于技术成就,而在于它能否促进人类精神的自由与文化的升华[12]。他的思想将科学与人文视为同一精神活动的不同维度,既不以科学消解人文,也不以人文限制科学,而是主张二者在深层次上相互贯通,形成以文化关怀为旨归的科学观。
三、科学与人文融通的实践维度:从杨振宁的言说到教育与文化行动
杨振宁科学与人文融通的思想也体现在他退休后所开展的系列行动中,涵盖了科学知识的普及、教育体系的革新,以及文化层面的交流与表达。他在许多公开的讲座和著述中,深入阐述了科学活动固有的审美价值和文化属性。例如,他多次细致讲解了规范场论中对称原理所体现的极致美感,以及物理学基本方程所蕴含的简洁性与和谐性。杨振宁将这些伟大的物理学核心方程赞誉为“造物者谱写的诗篇”,并指出物理学者在面对这些高度凝练的结构时,会油然升起一种“庄严感、神圣感,以及首次洞察宇宙奥秘的敬畏之情”[13]。这种富有诗意的表述,意在使非专业群体也能体会到科学探索与艺术创作在精神层面上的共通性,从而理解科学与艺术同为人类追求真理与美的心灵活动。与此同时,杨振宁也批评部分物理学家仅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数学,主张“数学之美的欣赏”与“物理之美的探求”应并行不悖,且贯穿学术生涯始终[14]。他还借鉴王国维的美学概念,对科学中“无我”的客观之美与艺术中“有我”的主观之美进行了区分,由此进一步揭示了科学美与人文美在审美结构上的内在同构性。
在回顾自身的科学探索历程时,杨振宁常以“妙悟”或“顿悟”等富有东方哲学意蕴与艺术气息的词汇加以描述。因为他认为真正重大的科学发现不仅依赖于长期的逻辑推演与理性计算,更需要那种瞬间的灵感闪现与心智通达的顿悟时刻[15]。正是这种心灵层面的共通体验,使他常将物理学家的创造过程与古典诗词的意境相提并论。他最为推崇的座右铭“宁拙毋巧,宁朴毋华”,源自北宋诗人陈师道的《后山诗话》,这一取向恰好揭示了他精神世界中科学理性与文学情怀的并存与互映[16]。在此意义上,杨振宁强调直觉、灵感与非线性思维的重要性,这一论述有效打破了“科学等于冷冰冰计算”的刻板观念,使科学活动被重新置于兼具人文温度与精神深度的广阔语境之中。
除了公开言说,杨振宁也将这一融通的思想落实到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具体实践之中。在参与清华大学等高校工作期间,他积极推动基础理科教育的深化与革新。他发现过度的学科专业化与工具理性导向使学生虽掌握了知识,却难以形成对科学的整体理解与历史洞见。因此,在《读书教学四十年》中提出,“教育的最高目标是启发独立思考与审美判断力。”在1999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上,他进一步提出其“理科教育改革”的构想,倡导将数学、物理等基础科学课程与哲学史、艺术史等人文学科相结合,以开阔学生的视野,增强其思维的深度与广度,从而塑造具备综合性思考能力的人才。他同时指出,高等教育不应仅致力于培养技术型人才,更应培育具有思想与精神追求的学者;科学教育的意义也不只是知识传授,更在于塑造人格与世界观。这一教育理念既承续了中国传统的通才教育精神,又对现代科学教育中过度专业化所导致的学科分裂进行了反思与回应[6]。
在思想和文化表达上,杨振宁将科学视为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之一,并积极推动科学与文化自信的融合。他多次强调“科学是文化最核心的组成部分”,意在反对将科学工具化、技术化、使其与人文文化对立的倾向。早在获得诺贝尔奖时,他就在致辞中指出自己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既以自己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又专注于现代科学。在他晚年的随笔集《曙光集》和《晨曦集》中,他流露出了对中华民族命运强烈的历史感与文化自信。他在《曙光集》序言中将旧中国比作“一个长夜”,而他这一代人幸运地“看见了曙光”;十年后,在《晨曦集》中他更是欣慰地表示“曙光已转为晨曦”。从“长夜”到“晨曦”,不仅是他对国家命运巨变的深切体认,更深刻地印证了他对于中国文化能够拥抱现代科学、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
作为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科学家,杨振宁积极倡导科学精神与文化认同的结合,为社会公众特别是中国学界树立科学文化自信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例如,在纪念钱学森诞辰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一个国家的科学精神,归根结底是这个国家文化自信的体现。”这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他思想的内在逻辑: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滋养,而文化的自信又需要科学精神的支撑。科学已深度融入人类认知结构,成为现代人把握自然、省思自身的基本途径,因而不仅是技术实践,更是文化建构的关键组成部分。科学由此被确立为承载国家精神气质与价值追求的重要维度,其发展水平直接映射出一个文明体系的自信程度与创新能力。
四、杨振宁“文理一体”观的再审视与未来指向
杨振宁所倡导的科学与人文融合理念突出强调科学探索的非功利取向与客观审美价值,这一立场有力彰显出科学的精神维度。然而过于强调科学的审美理想,可能弱化对其应用后果的批判性关注,尤其在技术转化过程中所引发的伦理困境、生态危机以及技术垄断等现实问题[16]。以核物理领域为例,尽管其理论结构在形式上体现高度的美学统一,但当其成果被用于制造核武器时,理论之“美”便与实际之“害”形成尖锐对立。同时,他的思想重心主要集中于理论物理学的本体论层面,面对人工智能、基因编辑等技术深度介入人类生活并引发主体性危机的当下,若科学与人文的融合无法有效回应技术对个体自由、社会结构与自然环境的深层冲击,该思想在应对当代复杂科技议题时,其解释力与实践指导作用或将面临一定局限[17]。
在全球化和文化多元的背景下,其融通理念也面对跨文化语境中的适应能力。杨振宁的批判立足于“中国为何未能孕育近代科学”这一历史命题展开,侧重从认知方式与哲学观念层面进行分析[18]。而当代文化研究强调,对文明的评判应是多元且非线性的。有学者认为,杨振宁对《易经》的某些解读过于简单化或缺乏对传统哲学内在逻辑的体认[19]。这意味着,融通并非简单的批判与吸纳,而应是基于深层文化理解的对话与共存。与此同时,杨振宁的融通主要集中在中西方文化精英层面的借鉴。而在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在多样化的文化生态中有效回应科学观念差异与文明张力,尚需发展更具包容视野与可操作路径的实践方案。
尽管存在前述的理论张力和现实限制,杨振宁的“文理本一体”思想仍为当前教育革新与科学普及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与可行方向。在教育领域,该思想为推动科学与人文学科的深度融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尤其对通识课程体系构建与跨学科人才培育具有指导意义。其核心在于超越将教育简化为专业技能训练的工具化取向,转而倡导培养兼具科学素养、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的复合型人才。具体实施中,理工科教学可融入科学史、科技伦理与科学美学内容,帮助学生在掌握知识体系的同时建立价值认知;在教学方法上,可吸收杨振宁所重视的“妙悟”思维,引导学生在逻辑推演之外发展直觉能力、创造想象与跨领域联想,进而体认科学探索与艺术创造在认知方式上的深层契合[20]。在科学传播层面,他的实践表明,有效的科学传播不应止步于知识传递,而应致力于提升科学的文化内涵与精神高度。传播者可借助对称、简洁、和谐等普遍性审美要素作为沟通媒介,增强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与情感共鸣,使科学从抽象知识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体验。更进一步,科学传播需拓展至对技术应用后果、伦理争议与政策选择的公共讨论,通过凸显科学家的伦理担当,引导公众意识到科学治理并非专家专属,而是现代民主社会中公民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推动科学真正嵌入公共文化结构之中[21]。
五、结语
杨振宁的贡献远超诺贝尔奖的光环,作为一位罕见的“文艺复兴式”人物,他对中西思想进行吸纳与整合,体现出“文理本一体”的理论特性。从“器、道、行”三个维度对其加以阐释:在“器”的层面,他以理性结构发现了自然界深层的数学结构之美;在“道”的层面,他以审美结构系统阐释这种美,并构建了沟通科学与人文的美学话语体系;在“行”的层面,他将对“美”的追求和对“善”的责任,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实践。纵观其思想演变与实践路径,可以看到“文理本一体”并非一个单纯的命题,而是一种贯穿科学认知、美学精神与文化哲学的深层逻辑。它反映了在知识爆炸和专业分工日益精细的当代,科学文化走向整体性理解的必然趋势。全球性挑战要求我们跳出单一学科的藩篱,整合科学的精确性与人文的价值判断。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杨振宁先生的思想如同永不熄灭的灯塔,对当代具有深远的启示作用。它呼吁当代的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必须以价值教育和美学教育为先导,培养具有跨学科视野和全学科意识、兼具科学精神与人文情怀的复合型人才6。只有重新认识到科学的文化属性和人文内核,才能真正实现科学与人文的相互滋养,最终推动形成一种理性、和谐、富有创造力的人类文明形态。本文希望能够以此激发学界对杨振宁思想的进一步研究,并为当代中国科学与人文教育的深度融合提供新的思路与理论支撑。
Abstract:
Contemporary society is witnessing an unprecedented rift between scientific rationality and humanistic values, while the thought of Chen-Ning Yang stands as a bridge spanning Eastern and Western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intrinsic logic of integr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in Yang’s thinking, framing it through the core concept of “the unit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This conceptualization serves not only as a cultural response to the “Needham Question” but also as an Eastern-informed remedy to the global schism of “the two cultures.” Yang’s legendary life and work demonstrate how cutting-edge scientific discovery (instrument), profound aesthetic appreciation (principle), and conscious cultural practice (action) can achieve a perfect synthesis, forming an intellectual structure characterized by the dynamic interplay of “rationality–aesthetics–culture.” In practice, through his scientific discours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cultural advocacy, Yang elucidated the aesthetic and cultural dimensions of science while championing the humanization of science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scientists. This study further refl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cultural studies, on the idealistic tendencies and practical tensions within his vision, thereby extending his ideas to offer insightful implications for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 contemporary science education and public communication of science.
Keywords: Yang Zhenning; Unity of science and the humanities; Science and humanity; Scientific aesthetics;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