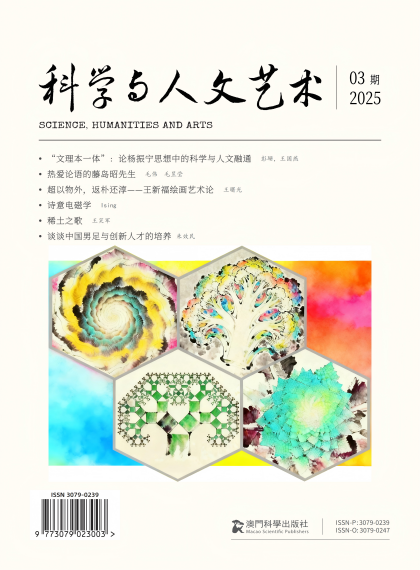曾有一中国学生获全额奖学金到美国名校攻读化学博士学位,某日在实验室里唉声叹气,旁边的美国同学表示了一下关心。他于是敞开心扉,谈起自己原本并不喜欢化学专业,美国学生听后非常吃惊,表示难以理解:“你既然不喜欢化学,干嘛还跑来学呢?”——意思是你为什么不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呢?中国留学生脸上露出“子非鱼,焉知鱼之苦也”的表情——意思是你丫根本不懂中国的国情,能上大学就不错了,专业上哪还有你挑挑拣拣的份儿!
近年来,一些美国大学传出不太愿意招收来自中国的博士研究生,原因主要在于后者的科研动力常常不足,即使比较刻苦和努力,却缺乏主动探索精神和自己的独特想法(中国留学生习惯对外国导师常说的一句口头禅是“请告诉我怎么做”,这让后者感到颇有些惊讶和不解:“我如果知道具体该怎么做,还要你来干什么?”),更出现一些博士生读研期间弃学、换专业、或毕业即改行的问题,不仅浪费大量宝贵教学科研资源,也反映出部分中国大学生即使到了博士生阶段依然还没有明确自己的专业兴趣和方向,可谓是“古人为学为己,今人为学为人”的又一个现实写照。

图1. 作者两次访问的丹麦奥胡斯大学校园一景
2022年夏中国男足一语成谶,居然大输越南队,已开始让人担心男足“没有谁不能输了”。果然2023年、2025年国足一再输给战乱中的叙利亚队,让广大忠实球迷几乎彻底“心死”。观察网上的评论,相当多的不满集中在男足队员的精神风貌上。按理中国男足改革多年,从举国体制,到市场机制,再到二者并行,国外各种大牌教练换了一茬又一茬,外籍球员也不断加入,却始终没有多大起色。毋庸置疑,足球运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精妙、且竞争激烈的团体体育项目,其队员的遴选、培养与创新人才的成长、选拔颇有可类比之处,比如以下三点。

图2. 作者访问的爱丁堡大学校园一景
首先,我们的体育、教育体系仍然相对缺乏因材施教的长期、全面培养意识,而更偏向于“拔苗助长”式的短期、应急选拔机制——有“好苗子”出现了,马上进行重点关照。这种急功近利的选拔机制的确也可以发现一些尖子人才,但往往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如何走捷径、找“灵丹妙药”、实现“弯道超车”等方面,始终相对缺乏全面长远、基础性、战略性的布局,也就难以有系统整体、持续不断的人才培养和涌现机制。而且,即使选拔出来的足球尖子,往往具备一些自身特色,但由于从小缺乏系统完整的专业训练和指导,导致其整体素质并不很高和全面。已经有足球外籍教练无奈地指出过这一点:一些国足队员的专业技术和配合问题不是进入国家队后能够解决的,这些问题原本应该是在长期专业训练中逐步解决的。
找“灵丹妙药”、靠国际“大仙儿”妙手回春常常只是应急,只能救得了一时,甚至一时都救不了。某男足外籍教练的年薪据说高达2亿人民币,试想一下,把这2亿元换成足球,每年给全国每一所中学、小学分发几个足球,让孩子们先玩起来、踢起来、爱上足球,是不是比单纯押宝国际大牌教练更可能带来长久持续的希望。不久前结束的2025年东京世界田径锦标赛,美国队以16枚金牌高居榜首,几乎占赛事总金牌数49枚的1/3,中国以零金牌收场。再次暴露出国内田径运动人才培养的青黄不接、多数时候靠零星天才运动员撑场子的尴尬局面。
不妨看一下我们“国球”的民众基础,笔者在中小学时代,一到放学大家就经常迫不及待地把几张课桌拼成一个简陋的乒乓球台,从书包里掏出自制的光板木头球拍,打起乒乓球来常常玩得不亦乐乎。管中窥豹,由此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乒乓球队可以在国际比赛中纵横捭阖、大包大揽各种金牌。我在美国访问期间多次组织周末徒步,有时会穿越一些居民小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居民家门前空地上都竖着篮球架子,可想而知篮球已融入了普通美国人的家庭生活当中。具备如此深厚的民众基础,难怪一骑绝尘、睥睨群雄的美国奥运篮球队有着“梦之队”的飘逸而梦幻的称号。

图3. 作者访问康奈尔大学时在校园附近湖边徒步
其次,回归事物本身,对足球、科研的爱好、激情、享受其带来的快乐更为重要。现在一旦要加强某方面的工作,如足球、计算机等,往往会提“从娃娃抓起”,看似长远,实则依然相当功利化,比如政策的倾斜、引导,金钱的大量注入、加持。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常常只是把追逐时尚和喜爱金钱更甚于足球、科研本身的人吸引进来,他们对足球、科研的“热忱”可能并非真正源自内心的渴望,亦难以持久与真正深入(中国男足的精神风貌常为人所诟病亦在于此)。国内常常比较熟悉的众志成城、集中力量组织攻坚战的科研创新实际上多属于工程创新类型,即知道别人已经做出来了,创新结果是确定无疑的,只要按照别人成功的方向持续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就会有相当大的概率成功,本质上是在重复他人的创新工作。这类创新活动相对于更加个性化、结果未知、效用完全不确定的基础创新或原始性创新(按严格定义即看不见结果、效用如何的创新)而言,二者在创新机制、方向识别、人才需求等方面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以发现哈雷彗星闻名的哈雷先生曾担任格林尼治天文台台长,有一次英国王后卡洛琳来视察,得知天文台在职人员的工资仍是50年前的水平,当场拍板要给予加薪,却被哈雷一口拒绝了,其理由是加薪后他无法确定将来申请天文台工作的人是出于热爱天文研究还是为了挣钱致富。笔者在英、美、丹麦多所大学做过访问学者,与西方学者的深入交流过程中时常能够感受到,西方大学往往是最聪明的人做着自己最快乐、最擅长的事情,这可能是中国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在科研原始创新方面至今仍存在相当差距的关键因素之一(想一想,大陆数千万的科学家中70多年来仅一人获得诺贝尔奖)。美国科学院曾经出版一本《怎样当一名科学家》的书,书中有个至今让笔者印象颇为深刻的例子:有位病毒学家说自己每天一大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想尽快跑到实验室里观察一下培养基里的病毒又有了什么新的变异,她还打了个十分贴切的比喻“就像小孩子早上爬起来立刻就抓起心爱的玩具大玩一通”。
科教界有一名言“优秀需要天赋,伟大需要激情”,这句话同样适合足球。看看电影中贝利小时候拿芒果练球的镜头、以及马纳多纳用橘子颠球的视频,令人惊异的不仅仅是他们的高超技艺和过人天赋,更在于他们享受足球、陶醉其中的气质和神韵,而挖掘、选拔、培养这样的天造之才首先需要创造适宜的环境让他们自身的才华、内在的热情充分激发、表达出来。
再次,无论教育还是体育都没有必要处处与他人比较,关键是如何把我们自己的内心渴望和自身的文化精神表达出来,成为更好的自己。奥运会(Olympic Games)原本就是由一个个“游戏”(game)组成的,其他附加的诸如商业价值、时尚导向、民族自尊心、政治含义等多是后来不断由外部注入的。谷爱凌在夺得冬奥会冠军后说道:她最大的目标不是超过其他人,而是希望打破自己的界限,并享受运动带来的快乐——这才是真正的“为学为己”之道。姚明当年在NBA打球时,曾被美国电视主持人调侃,中国十多亿人口怎么挑不出5个篮球打得好的?姚明回敬道,美国3亿男女怎么也选不出2、3个乒乓球打得好的呢?实际上,即使体育强国美国同样有不少奥运短板,比如美国男足亦战绩平平,泯然众人矣。
2017年暑假我在俄克拉荷马大学访问,刚好赶上美国橄榄球全国联赛的决赛在该大学举行。假期里原本十分冷清的大学所在地Norman小镇几乎人山人海,旅店爆满,到处是房车、轿车,当地各家各户都出租停车位,连许多小朋友也在家门口售卖饮料赚钱。美式橄榄球并非奥运项目,但在美国却极受民众追捧,俄克拉荷马大学橄榄球队拿过7次全国冠军,其明星球员的奖学金甚至比校长的年薪都高。实际上,即使贵为奥运项目也没有那么神圣和重要,更值得引起我们关注的也许应该是:这项运动是否是我们真正喜爱的、并能够充分展现和畅快地表达我们自己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气质。只有不自信的人才会处处与他人较劲,甚至以己之短比人之长,并斤斤计较外人的评价。

图4. 作者四次访问的俄克拉荷马大学钟楼一景
中国多年前已经提出“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随着我们的发展进步面对新的未知领域,很难再实施以往的后发优势、弯道超车等策略,其投资方向常常变得犹如“老虎吃天,无处下嘴”,因而需要对创新活动及人才培养有更加深入、全面的认识。许多天才的成长过程往往是非常个性化的——“风起于青萍之末”,难以按照固定模式训练出来。中国创新人才培养和选拔的一个思路应是将更多注意力放在基础制度环境的认知和建设方面,培养是各成其是,选拔是为我所用。与其一再强调人才选拔的前瞻性、针对性、引导性,不如增加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多层次性和多样性;与其押宝重点扶持,不如放手广种薄收,各成其才,方为大用。慧眼识人才的早期选拔固然可喜可贺,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培养更是难能可贵。
同时,人才培养选拔也不仅限于政府体制,应有更加广阔的全民体制视野(社会、市场、私人等),因为给每一个个人和机构以尽可能平等、多元、自由的成长、发展机会所蕴含的潜在的无限可能性——各适其天、各成所是,成龙成虎任方便,才是社会进步、体育昌盛、创新开拓真正取之不竭的人才涌现之源。
Abstract:
This article talks about three perspectives on talents education between similarities of Chinese man football and science innovation in China. First, talents are produced from systematic and long-run education, not just from temporary selection. Second, innovation motivation from inner interest and love is far more important and valid than outside financial support. Third, the final purpose of education including physical education is to be a better self, not always to compare with others which in fact usually is limited by others. As a result, we should recognize the true meaning of innovation and education again.
Keywords: Chinese man football; Innovation; Talent education;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