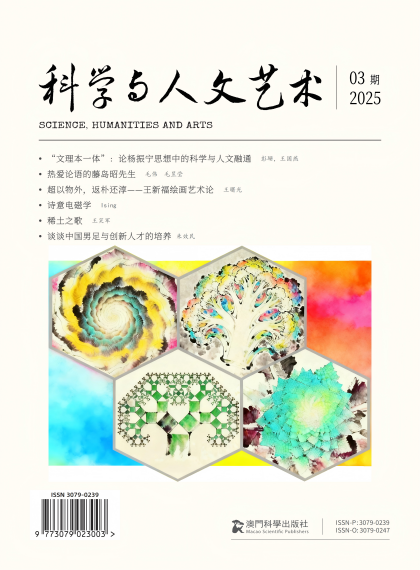数学中有一类正整数对被称为“亲和数”(amicable numbers),定义为每一个数的除自身以外的所有因子——即所谓真因子(proper divisor)——之和等于另一个数。最常见的例子是其中最小的一对:(220, 284)——因为220的真因子之和1+2+4+5+10+11+20+22+44+55+110为284,而284的真因子之和1+2+4+71+142则为220。
像“亲和数”这种将两个正整数的因子交叉联系起来的概念,在我眼里是带有几分游戏色彩的花哨概念,以往较少涉猎,亦不甚留意。
不过前一阵闲读的一本书却让我在“亲和数”上意外花掉了一点时间。苏格兰作家鲍斯韦尔(James Boswell)曾在日记里写过,他不应该活得比能够记录的更多,否则就是浪费。美国作家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也在The Early Asimov一书的序言里表示过,他绝不会将自己的深层情感写进日记,因为深层情感若只能浪费在日记里,他还当作家干吗。我虽不是作家——起码不是职业的,好歹也算是喜欢在闲暇时写点东西,对这两位的说法,我颇有同感。对我来说,花掉的时间——起码就自主花掉的时间而言——若完全不诉诸文字,也有一种浪费的感觉。
为避免浪费,我坐下来写这篇闲读记。
我闲读的那本书叫作《一个人的出版史:1982‒1996》(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9月),作者俞晓群是一位知名出版人。这位俞晓群——我从他这本书里才知道——本科的专业是数学,并且很喜欢数学史。因为这层渊源,他这本日志体的书既是一个出版人的“出版史”,也是他作为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兼数学史爱好者的阅读及数学科普写作史。
在俞晓群这本书——以下简称“俞书”——的1983年7月19日的日志里,他提到自己读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克莱因(Morris Kline)的《古今数学思想》一书。在为该则日志所撰的补注中,他援引自己2014年撰写的一篇文章,称自己发现了《古今数学思想》中的两处小错,其中之一是书中所列的最早的三对“亲和数”之中,“第二对17298和18416、第三对9363584和9437056,都是错的”。而更吸引我注意的则是接下来的两句话:“我写信给出版社,一位参译的北大教师回信感谢;再版时,出版社修正过来。奇怪是近些年此书又再版,我发现出版者将错处又改了回去。”[1]
俞晓群提到的《古今数学思想》是依据剑桥大学出版社(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2年出版的英文著作Mathematical Thought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翻译的中文版,共分四册,所提到的小错出现在第一册(因此下文凡提到中文版,都将只指第一册),初版于1979年10月。《古今数学思想》是中英文都有相当知名度的书,尤其中文版,在图书相对匮乏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是鹤立鸡群般的好书。
这样的好书在我的书架上自然也不会缺席——我甚至万里迢迢将之带到了美国。因此读到俞晓群的上述文字时,很自然就拿下来核验了一下。
不过,我昔日有过的一套1979年版的《古今数学思想》(是父母给我的礼物,甚至还带了父亲的题字)在早年往美国海运时寄丢了,如今这套是后来补买的2002年版。俞书提到的那两对“亲和数”在该版上分别是(17296, 18416)和(9363584, 9437056)。除这个2002年版外,此书还有一个2014年版,我有扫描电子版,其中所列的数值也是一样的。除17296跟俞书中的17298略有出入外,这些数值跟被俞书称为“都是错的”的数值完全相符。从时间上看,俞书所说的“近些年此书又再版”应该就是指这两个版本(或其中之一),数值上的基本相符则大体印证了“出版者将错处又改了回去”的说法。
但既然知道书中那两对“亲和数”是错的,我自然要顺便注上正确的,免得将来忘了此事后会被误导。于是我上网查了一下(“亲和数”的数值在网上有很可靠的数据源,比查书方便得多)。这一查让我大吃一惊:书中那两对“亲和数”,即(17296, 18416)和(9363584, 9437056),其实是正确的!
如果那些数值其实是正确的,那么俞书所说的早期版本“都是错的”,及晚近版本“将错处又改了回去”是怎么回事呢?莫非是英文版存在错误,俞书以英文版为基准(俞晓群在同期的日志里提到过自己有阅读英文原版书的能力,故以英文版为基准也并非不可能)而对中文版作出了错误判断?
为检验这种可能性,我当即查阅了该书的英文版,结果发现那里列出的那两对“亲和数”分别为(17296, 18416)和(9363548, 9437506)——果然存在错误,但只有后一对是错的(下横线划出的是错误部分),前一对则是正确的。这里顺便说一下,该书的英文版除1972年版外,还有一个1990年版——是首次出平装本时的版本,但两者所列的那两对“亲和数”是相同的——即存在相同的错误。
与此同时,为了搞明白俞书中17298这个跟上述中英文版本全都不同的数值从何而来,我对早期的中文版也进行了排查,结果发现,《古今数学思想》的1979年版(再次提醒一下,所指皆为第一册)在1979‒1985年间共有过四次印刷,所列的那两对“亲和数”的数值分别为(各次印刷的出版年月列在括号里,下横线划出的则是数值里的错误部分):
第一次印刷(1979.10):(17926, 18416)和(9363548, 9437506)
第二次印刷(1982.08):(17926, 18416)和(9363548, 9437506)
第三次印刷(1984.12):(17296, 18416)和(9363584, 9437056)
第四次印刷(1985.09):(17296, 18416)和(9363584, 9437056)
归纳一下的话,那么在我排查过的所有中英文版本里,就那两对“亲和数”而言,英文版是前一对正确,后一对错误;中文1979年版的第一、二两次印刷是两对都错,其中第二对错得跟英文版一样,想必是翻译时的继承错误,第一对则是中文版独有的错误,可能是译者的笔误或排版错误。中文版自1979年版的第三次印刷开始就订正了全部错误——包括摆脱了始终不曾订正的英文版里的错误,后来的2002年版和2014年版也是完全正确的。
用上述归纳对比俞书的说法,则首先可以大体断定后者的17298应系笔误——因为所有中英文版本里都不曾出现过这一数值。其次,俞书的说法是对1983年7月19日日志的补注,所针对的中文版次想必是截至当时能读到的——即1979年版的第一、二两次印刷。那两个版次里的那两对“亲和数”确实都是错的——从而俞书的说法在定性上是正确的,只是在罗列具体数值时张冠李戴成了正确数值(除了17298这一笔误)。这里还有一个细节需要提一下,那就是1979年版的第一、二两次印刷中的那两对“亲和数”虽然都是错的,但第二对由于错得跟英文版一样,俞晓群需要知道那两对“亲和数”的正确数值——而非仅仅以英文版为基准——才能看出其错误。俞晓群当时有可能知道那两对“亲和数”的正确数值吗?答案是:很有可能。因为俞书在1984年12月5日的日志中,收录了当天刊出的俞晓群的一篇有关“亲和数”的科普,其中列出的那两对“亲和数”是正确的。考虑到一篇文章从撰写到刊出要经过许多环节。1984年12月5日刊出的文章,其撰写时间应早于1984年12月才出版的首次包含那两对“亲和数”正确数值的1979年版第三次印刷的《古今数学思想》。因此,俞晓群是通过独立于《古今数学思想》的渠道就已知道了那两对“亲和数”的正确数值——至于具体是什么时候知道的,自然非我所能知晓,但“亲和数”算不上冷僻话题,那两对“亲和数”更是有一定的故事背景,常被数学史和数学科普提及,作为数学专业的毕业生兼数学史爱好者,很早就知道也是完全可能的。
至此,对俞书的说法,似乎可以给出这样一种梳理:俞晓群在阅读1979年版第一或第二次印刷的《古今数学思想》时,由于知道那两对“亲和数”的正确数值,于该书第三次印刷之前的某个时候发现了书中数值的错误,并“写信给出版社”,得到“一位参译的北大教师回信感谢”。《古今数学思想》也因此从1979年版第三次印刷开始就订正了那两对“亲和数”的数值——连继承自英文版的错误也一并订正了。不过俞书在罗列错误时将正确数值(除了17298这一笔误)误列为错误(考虑到俞书的说法系时隔三十余年之补记,误列亦不算离奇),并因此作出了“近些年此书又再版,我发现出版者将错处又改了回去”的错误判断。这种梳理自知是有些风险的,弄得不好甚至有对作者不敬之嫌,但话题因俞书而起,不梳理似乎有头无尾。不过,无论梳理是否正确,上述文字的实质目的只是记叙闲读时花掉的那点时间,同时也算是对《古今数学思想》一书中文版次沿革的一点小钩沉。
这篇“闲读记”到这里原本可以结束了。不过我前一阵受一位友人之邀,打算写一些新的数学类文字,故决定将这篇文字里的数学部分稍稍延展一点,再多聊几句“亲和数”这一概念——尤其是它的起源。
“亲和数”的定义在开篇时已经介绍过了,我并且还说了,像“亲和数”这种将两个正整数的因子交叉联系起来的概念,在我眼里是带有几分游戏色彩的花哨概念。事实上,当我看到这一概念时,立刻就觉得既然能搞出这种概念,何不进一步将多个正整数的因子连环联系起来。当我这样设想时,是故意用一个在我看来很随意的延拓,来作为对这一概念的逆反的,但撰写本文之前我查了一下,发现将多个正整数的因子连环联系起来的概念还真的有,甚至已有专门的名字,叫作“社交数”(sociable numbers),与之相类的还有另外一些花哨概念,比如婚约数(betrothed numbers)、佩服数(admirable numbers),等等,简直有一种凡想得到的东西都被人想到过了的感觉。[2]
对“亲和数”这一概念的起源不甚熟悉的读者也许会觉得,这种花哨概念是研究者多到一定程度,僧多粥少之下,挖空心思发掘课题时才臆想出来的,历史不至于太久远。[3]其实完全不然,“亲和数”这一概念可以回溯到数学领域里久远得不能再久远的古希腊先贤: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
“亲和数”这一概念可以回溯到毕达哥拉斯倒也并非偶然——或者换个角度也可以称之为极度偶然。因为毕达哥拉斯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哲学教条是“万物皆数”(all things are number)。既然宣称“万物皆数”,于是——据传说——就有人拿一个看起来跟“数”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诘问道:什么是友谊(“what is friendship”)?而毕达哥拉斯——仍据传说——则回答说:友谊就像220之于284(“friendship is as 220 is to 284”)[4]。
不过,当我们谈论毕达哥拉斯时,必须非常小心,因为毕达哥拉斯不曾留下任何文字。不仅如此,他还有一个庞大的“追星族”,其核心人物构成了所谓毕达哥拉斯学派(School of Pythagoras)。后世流传的许多毕达哥拉斯的成就或见解究竟是出自他本人还是学派,甚至是否真实,往往都早已被久远的时光涂抹成了糊涂帐。具体到“亲和数”这个概念,并无任何证据显示它出自毕达哥拉斯本人,我所知道的将之跟毕达哥拉斯联系起来的最早的文字,是出自公元三世纪(245‒325)的哲学家杨布里科斯(Iamblichus)。杨布里科斯是曾经为毕达哥拉斯立传的早期人物之一,算得上毕达哥拉斯专家,但他跟毕达哥拉斯之间横亘了八九个世纪,有如我们跟中世纪后期的时间间隔。
杨布里科斯将“亲和数”跟毕达哥拉斯联系起来的文字,是写在了他对活跃于公元一世纪晚期的哲学家尼科马库斯(Nicomachus)的《算术概论》(Introduction to Arithmetic)一书的评述里,核心是下面这几句话:
他们将某些数对,比如284和220——其中每一个的部分可以生成另一个,称为“友好的”,并赋予它们美德及优良品质。这是依据了毕达哥拉斯对友谊的定义。因为在被问及“什么是朋友”时,他回答说“另一个自己”。这显然跟这些数字的情形相符合。
这几句话跟我们前面提到的传说大体相似——事实上,后者有可能正是从这几句话衍生出来的,因为讲述那些传说的文字但凡提供出处,提供的往往就是杨布里科斯的这几句话。不过,这几句话的主语是“他们”,因此哪怕不考虑时间久远带来的不可靠性,也只是将“亲和数”的概念归于毕达哥拉斯学派而非毕达哥拉斯本人。由上述文字及传说来看,如果不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恰好有一个“万物皆数”的教条,就不会有人拿“万物”之一的“友谊”来诘问——哪怕问了也不可能得到(220, 284)这样一对“亲和数”作为回答。因此,“亲和数”这一概念可以回溯到毕达哥拉斯是有特殊缘由的,既可以说是“并非偶然”(因为一旦主张“万物皆数”,则设想出表示“友谊”的“亲和数”就比较顺理成章了),也可以称之为“极度偶然”(因为在古希腊的“诸子百家”里,恰好有一家主张“万物皆数”纯属偶然)。
以上就是“亲和数”这一概念的起源。发现“亲和数”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早期对“亲和数”的发现无论在方法上还是结果上都是零星的。被《古今数学思想》所介绍,并被俞晓群写入“出版史”的那两对“亲和数”,即(17296, 18416)和(9363584, 9437056),正是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那对(220, 284)之后最早被发现的“亲和数”,其发现起码可分别回溯至十四世纪的穆斯林学者阿尔丁·法里西(Kamāl al-Dīn al-Fārisī)及十六世纪的伊朗数学家亚兹迪(Muhammad Baqir Yazdi)。到了十七世纪,那两对“亲和数”又分别被法国数学家费马(Pierre de Fermat)于1636年及法国哲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于1638年所重新发现——我在前面所说的那两对“亲和数”有一定的故事背景,指的就是这段被重新发现的历史,它使得很多人——包括《古今数学思想》的作者克莱因——将费马和笛卡尔视为了那两对“亲和数”的发现者。这些早期发现的零星性可以从一个简单事实看出来:很多更小的“亲和数”反而是更晚近才被发现的。比如除(220, 284)之外最小的一对“亲和数”(1184, 1210)居然躲过了费马、笛卡尔、欧拉(Leonhard Euler)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的法眼,直到1866年才被一名连生平资料都很难找到的十六岁意大利年轻人帕格尼尼(B. Nicolò I. Paganini)所发现!
不过到了如今这个电脑时代,穷举法大行其道,像(1184, 1210)那样的“捡漏”已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亲和数”的研究并非热门课题,自毕达哥拉斯之后隔了约两千年才发现第二对——即(17296, 18416),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人们所发现的“亲和数”也只有区区几百对。但到了2023年,据不列颠百科全书网站介绍,这一数目已膨胀到了1,227,869,886对,其中涵盖了一万亿亿(1020)以内的全部“亲和数”。除这种系统涵盖外,人们也发现了很多零星的“亲和数”,其中的某些达到了惊人的大小:比如2022年发现的一对“亲和数”包含了一个位数多达56,259的巨大数字,写成中文的话,需要用到成千上万个“亿”字!
既然已找到如此之多、如此之大的“亲和数”,一个很自然的问题就是:发现“亲和数”的道路会有尽头吗?或者换句话说,“亲和数”有无穷多对吗?这个类似于孪生素数猜想的问题虽远没有孪生素数猜想出名,却也是一个未解之谜,是留给未来数学的一个美丽悬念。
在结束本文之时,我要向帮助我搜寻《古今数学思想》早期版本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王涛副研究员表示由衷感谢。
Abstract:Starting with a casual reading that revealed an error in Morris Kline’s Mathematical Thought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on amicable numbers, we combed through the early Chinese editions of the book. We also briefly introduced the origin of the concept and the history of the computation of amicable numbers.
Keywords: Amicable numbers; Mathematical Thought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Pythagoras